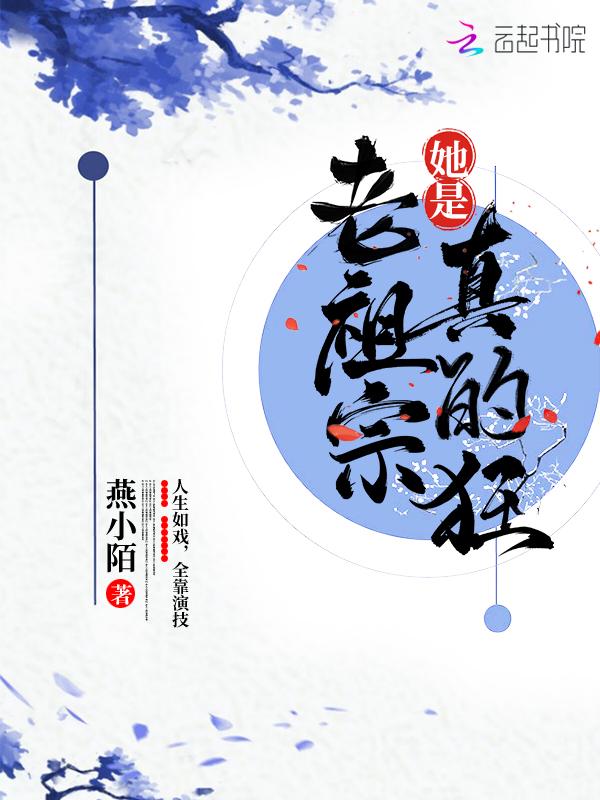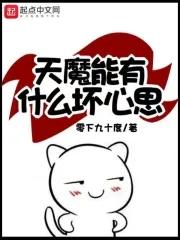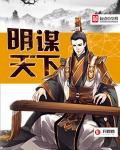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御前女官 > 5060(第16页)
5060(第16页)
这是她的第一封折子,往后会有更多,此刻她对皇帝也不得不生出一丝感激,这若是在先帝时,她想都不敢想。
皇帝的决策只是一句话,但底下人办事就不能只靠嘴了。
赵长宁和皇后几番商议,又向皇帝请旨,计划在半年里裁撤三千宫人,当然,太监占多数,宫女则基本是年纪到了,愿意出宫的为主,只占少数。
裁撤宫人还算简单,毕竟他们没有办法反抗,只能听天由命,而皇后仁德,善后有方,勉强安稳。
但贵人们就很难伺候和说得通了,得知连饭食都要裁减,许多自小锦衣玉食的贵人都很不满。
尤其是永和宫的昭仪娘娘,她宁愿每天自己多拿出几十两银子,让专人去宫外采购,也不肯裁减用度,更别提丝绸瓷器等御贡了,直言大庸也没有穷到这种程度。
皇后对此十分无奈,更多的是愤怒,这么些年被她按压着,偏偏她是皇后,还要大度容忍。
“她这是故意和我对着干呢,这事儿必须禀报给皇上,怎么偏她金贵了呢?”
赵长宁轻轻摇头,劝解道:“娘娘,就让她去吧。”
皇后理智回笼,看了赵长宁好一会儿,总算是恢复冷静,“你说的话我都懂,我也知道你说得对,但这口气,我实在忍不下去。”
赵长宁并未再劝,她知道皇后自己能想明白。
她并不是不愿意帮皇后,而是没有时间,更觉得没有必要,昭仪娘娘有点手段,但都太过儿戏,也没有大局观念,昭仪忘记了,这是皇宫,不是十四皇子府了。
先帝曾教过她,这样爪牙软趴趴的女人,在宫里活不长久。
接下来,赵长宁有她自己的差事。
因着她提议要将丝绸瓷器等御贡交由市舶司运出,皇帝便大胆决定将此事交给她去办了。
其实,是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差事,不用想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,但赵长宁不怕,这是她接到的第一个正式的差事,她决心一定要办好。
她也仔细思虑过,这事儿比织造局那个烂摊子要好收拾些,毕竟胡狗儿都拿不下那些丝绸。
赵长宁自然是和皇后站一边的,她意有所指道:“娘娘,您最近就多观察永和宫,到时候挑个好时机,我会想办法请皇上去的。”
皇后深深的看了赵长宁一眼后,拉着她的手,松了口气,“长宁,幸好有你在。”
赵长宁从她眼里能看出些许慌乱。
亲蚕礼后,已是二月将尽,春寒料峭。
赵长宁接下差事已经有段时日,为此特意请示了皇帝,换了个可以自由出入宫闱的腰牌。
皇帝大手一挥,“长宁,朕可将此事全权交给你办,莫要叫朕失望。”
赵长宁叩谢皇帝信任后,又去了市舶司,终于见到了市舶提举方大人,此人是先帝时便在任的,在市舶司待了十年,对码头和货物十分熟悉。
她盈盈一礼,“方大人,今日终于得见,先帝还曾夸过你,说有你方文海在,市舶司便不愁买卖。”
方大人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,面容慈和,笑脸不断,对赵长宁的到来并不惊讶,显然早有准备。
“女书令,真是久闻不如一见,今日得见,真叫方某汗颜。”
赵长宁连连摆手说不敢,“长宁只是协助,主事还得是方大人。”
方文海头摇得像是拨浪鼓,“不不不,女书令是皇上亲令而来的监事,今日这御贡一事,还得女书令主导,方某一切听女书令的。”
赵长宁敏锐察觉这里头有事,此人推脱的话出口太快,但她面上不显,只随着方文海在市舶司衙署转悠了一圈。
方文海根本不急着让她接触事务,连货仓都不带她去看看,而是说带她去接风洗尘,先吃好喝好再干活儿。
“女书令莫要着急,为皇上办差,都是细水长流,咱们来日方长呀。”
赵长宁想着尽量融入进去,也就跟他四处晃悠,吃吃喝喝好几天,终于受不了了。
云生也觉得奇怪,“姑姑,怎么老是要您吃吃喝喝,他们不用办事儿吗?”
赵长宁知道这里头定然有事。
她这天将饭局给推了,只说身体不适,却转头便带着安义和云生直奔货仓而去,一般这种地方,搬运工都很多。
她拉着云生跟安义,嘱咐道:“搬货卖力些,休息的时候多交谈,打听这是哪里来的货物,要搬去哪里之类的,总之不管问到了什么,都要回来跟我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”
云生嘴巴紧抿,眼神万分坚定,跟着安义一起混在人群里。
很快,云生就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