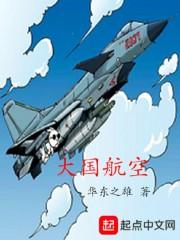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御前女官 > 8090(第12页)
8090(第12页)
殿中唯有龙缸冰盆中的冰块消融之声,至于蝉鸣,勤政殿周边的蝉早就被粘完了,博山炉上紫烟袅袅,阒静无音。
“起来吧。”皇帝摆摆手,语调倒还算平静,“方才高首辅说,他愿意退掉所有圈占的土地,辞去首辅之位,高家现如今的所有,他都不要了,只求孙儿平安。”
赵长宁额头触地,“雷霆雨露,皆是皇恩,高首辅毕竟是两朝老臣,劳心劳力,若手段太过,恐怕会引起朝臣动荡,皇上三思。”
皇帝勉强点头,感慨道:“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,高晨知法犯法,按照大庸律,当杖一百,徙千里……”
赵长宁叩首,道了句“皇上仁慈”,便再未开口。
今日高赟如此做,还当着所有人的面,无疑是将这件事划了停止线,以一己之力挽回动荡之势,也救了不少人性命,如此,更赢得了朝臣的感恩之心。
此刻怕是皇帝想动,也动不了,果真是老狐狸。
但终究,煊赫一时的高家,顷刻如山倒,如同当初的胡党,牵连也颇广。
赵长宁无奈接了清点高家的差事,也只有她接,幸好还有女官支撑,否则这差事都没人帮她。
就在这个重要时候,许家闻又跳出来,再次在朝堂撒了把火,又参了孙之道一笔,言及他家的地,也远远超过应有的。
孙之道气得当场暴跳如雷,怒骂都察院的人像是疯狗,尤其是许家闻,疯狗中的疯狗。
他还提及,都察院里也有不少人,手里有地,“哼,别真当我是个大老粗,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而许家闻的折子,引起了都察院大部分御史的同仇敌忾,御史们向来伶牙俐齿,尤其是宋宗恒,一人能抵十人。
最后还是皇帝出面阻止。
皇帝面色颇伤心,语调很是失落,似是对高赟不在而难过。
“今日朝堂动荡,民间谩骂,皆因圈地而起,高首辅已经退还了所有不该得的地,也承认了有错,诸位若主动退还,朕便不做追究,若还要骚动,那就不要怪朕动真格了。”
他的话,总算阻止了那些争吵怒骂,杀鸡儆猴的事儿已经做了一次,足够了。
赵长宁的眸光在许家闻和皇帝之间转了转,心中轻叹。
还是先帝老成精,老臣不过是皇帝的磨刀石,试金石,难怪当初说什么皇位无论是和平过渡,还是血腥上位,都要经过血的洗礼,无一例外,果真一字不错。
不过这也便宜了她,激流之下,她才能逆流而上,正是因此,她再次站上朝堂的时候,没有人敢忽视她。
谁都知道高家倒下的事儿有猫腻,一切都来得太快太凶,证据一个比一个狠,没有一点反应时间,事到如今,只剩零星求情的声音,也被淹没在人潮骂声里。
大家面对年轻的皇帝时,再次意识到,皇帝的手段也一点不差,根基也一点一点扎稳了。
面对她时,也会好好地打招呼,甚至有些事会主动请她参与进来讨论,而不是像从前那样,吆五喝六的直接让她闭嘴,也没有人说什么女子不能议政的话题。
似乎全都默认了,她可以与他们并肩而立。
当然,背后任何难听话都有,不过赵长宁只当听不见。
面对这些,赵长宁全然接受,这是她应得的,也是她该承受的,权力是双刃剑,她早就明了。
想要权,就得舍弃一些东西。
只是清算高家的时候,阻碍不小,面对的风言风语也不少,对权贵来说,这一次损失重大,谁来清算都要挨骂,她也干脆一并受了。
宋环当仁不让的随着赵长宁一起办差,毕竟参高赟的,就有她父亲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“你们去那边,将那些瓷器和书画都登记造册,一个都不许漏了。”
她将人都打发走,一扭头,就看到跪地哭泣的高家下人,过来帮忙的官吏亲眷,还有外头围观叫好的百姓。
赵长宁犹如玉面阎罗般站在那,静静地看着安义带人一箱箱的搬东西,哭喊声求饶声不绝于耳。
主家已经走了,这些被迫留下的下人,结局好不到哪儿去。
宋环朝她走来,看着面前凄凉悲怆的场景,喃喃道:“姑姑,你可小心了,将来史官笔下的你,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赵长宁若有所思。
“祸乱帝心?把持朝纲?心狠手辣?无恶不作?我不在乎,历史浩繁如烟,厚重无比,我能留下一笔,已经是千难万难,多的是连一笔都没有的普通人,如车轮滚过带起的泥沙,风一吹就没了。”
“史官笔下的恶女你是做定了,不过你也别担心,记载下来的东西,只要有人感兴趣,就一定会深挖,所以民间对你的赞誉很重要……”
宋环望向门外伸着脑袋的百姓,一张张淳朴的脸上满是好奇,他们或许也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作用吧?
史书史料不就是这样,只能供给后人看。
她轻笑道:“可别小瞧了这些外在的东西,只要百姓深感其恩,为你流传下哪怕一首诗,一句话,那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你的事迹,比如那始皇帝,史官多有骂名,但民间野史无数,总能窥其一角,看出他这千古一帝的磊落英明,那内舍人也是一样,史料少不代表后人蠢,但是有一点,你应该注意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