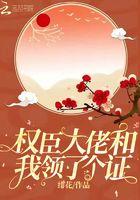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魏晋不服周 > 第201章 上桌吃席7(第1页)
第201章 上桌吃席7(第1页)
金谷园农庄那个简陋的大门两旁门柱上,分别写上了一则对联。
左边一联写着:天生万物以养人。
右边一联写着:人无一德以报天。
当天那些肥羊被关进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,所以这些人并没什么感觉。。。
夜雪悄然落于建康城头,檐角铜铃轻响,如低语回荡。阿禾未眠,独坐灯下,手中摩挲着那卷《莲塘冬日笔记》的抄本??天子彻夜翻阅之书,正是她当年在祁连山脚、油灯昏黄中一字一句写下的心迹。如今它已不再是私藏的孤本,而是被刻入宫墙碑林,供百官诵读,甚至成为新设“普教御史”的必修典籍。
窗外忽有叩声,似竹枝敲窗。她抬眼,见晓禾披雪而入,发梢凝霜,怀中紧抱一匣。“刚从北地来的人,”她喘息未定,“走冰河九日,说若迟一步,消息便要被截在潼关。”
匣启,内藏三封密信,皆以火漆封缄,印纹为一只展翅的鹤??那是西域法治联盟最隐秘的传讯系统。第一封来自高昌老塾师韩五娘,字迹颤抖却坚定:“阿禾姐,你走后第三月,县令仍拒开义学。我率二十女童跪于衙前七日,食雪饮风。第八日清晨,他竟亲携钥匙前来,说‘朝廷诏书到了,不敢违’。现已有四十七名女子入学,最小者五岁,最大者是我六十二岁的母亲。我们每日第一课,仍是写名字。她说,她叫‘韩阿姆’,不是‘韩家婆子’。”
第二封是乌仁娜自敦煌寄来,附图一幅:昔日焚毁的夜读堂废墟之上,已立起一座木构学堂,屋顶覆以彩布拼成的“律”字。信中写道:“炭笔罐已打开,三百二十一根笔头分予孩童,每人持一支,誓写满千页方肯放下。昨夜有个八岁男孩抄完《选举令》全文,哭着问我:‘姐姐,我现在能选官了吗?’我答:‘你不能选,但你能记。记住谁不许你选,将来便不可饶恕。’”
第三封最薄,却最沉。仅一行字:“王允之现身洛阳,托名医者,开设‘正音书院’,专收寒门子弟,讲授‘忠孝为先,识字次之’。其徒出口成章,皆言‘阿禾乱法,妇人干政,悖逆纲常’。”末尾无署名,只画了一枚断裂的铜尺??那是早年黑水盟用来标记叛徒的暗号。
阿禾久久不语,指尖抚过那断尺图案,仿佛触到旧日刀锋。良久,她吹熄灯芯,起身推门而出。寒气扑面,庭院积雪盈寸,映得天地清冷如镜。她缓步至院中石桌,取出周延地图铺展其上,以朱砂笔在洛阳方位重重一点,又在其周围圈出并州、兖州、豫州三地,低声自语:“他们换皮不换骨,改口不改心。从前用刀压人,如今用书驯人。”
次日清晨,李慎匆匆登门,官袍未整,神色凝重。“宫里出了事,”他压低声音,“昨夜太子书房失火,烧毁半架典籍。司礼监查勘现场,发现起火点正是那幅《万灯祭法》复原图所在。更蹊跷的是,守夜宦官全数中毒昏迷,唯有一人苏醒,断续说出两字:‘正音’。”
阿禾冷笑:“好一个‘正音’!不是矫正乡音,是要正天下之音,让所有人只听一种话,只信一种理。”她转身唤来晓禾,“即刻召集火种队残部,我要重启‘巡讲十三州’计划。这一回,不止讲《普教学令》,更要讲《正始律》真义,讲‘官出自公选’,讲‘法属万民’。他们想用书院洗脑,我们就用脚步破咒。”
七日后,春社未至,阿禾已率三十骑离京北上。队伍不再浩大,却更为精锐:有曾跪雪求学的老妪,有自焚私塾中逃出生还的塾师,有精通音律的盲童,还有两名原属黑水盟、后被感化归正的文书吏。他们携带着新制的“律镜简册”??将十二篇律文拆解为通俗白话,配以图画故事,专供乡野孩童诵读。
首站抵寿春,正值当地举行“开蒙礼”。按新规,七岁童子须入官办义塾,然族老把持学堂,教材仍用旧版《孝经衍义》,删去所有涉及平等、诉讼、民权的内容。阿禾未惊动官府,只命人在城南空地搭起布棚,挂出一面巨幡,上书四个大字:“你说得对。”
围观百姓不解,她便请一名十岁女童上台,问:“你叫什么?”
“张氏二丫头。”女孩低头。
“这不是名字。”阿禾温和道,“这是编号。你的名字,是你自己取的。”
女孩犹豫片刻,小声道:“我想叫……念书。”
众人哄笑。阿禾却郑重记下,转身展卷:“今日第一课,《正始律?民事篇》第一条:‘凡人皆有名,名自主立,非由主赐。’谁说她不能叫‘念书’?谁说她不该读书?”
随即,她命盲童击鼓,每鼓一声,便有一人上前讲述自己因无知而受欺的经历:有人田产被夺,因不懂契律;有人妻女被卖,因不知禁令;更有老农痛哭:“我替东家种了四十年地,去年他一句话就把我家赶出门,说我‘非本族血脉’。可我爹妈葬在这土里,比我姓还老!”
声声泣血,闻者动容。当夜,三百户联名请愿,要求更换教材、重选塾师。第三日,县令不得不亲自到场,承诺三日内整改。阿禾临行前,在学堂墙上题字:“知识不是恩赐,是权利;学习不是服从,是觉醒。”
一路北行,类似场景接连上演。至谯郡时,遭遇“正音书院”弟子当街辩论。对方少年才俊,引经据典,称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“庶民识字易生妄念”。阿禾不怒,只请出那位名叫“念书”的女孩,让她当场背诵《治理律》全文,并问她:“你读这些,是为了造反吗?”
女孩摇头:“是为了以后,别人再也不能骗我说‘这地不是你的’。”
围观士子默然。有老儒叹息:“昔年孔子有教无类,今人却以教限人,岂非辱没圣门?”
四月初八,队伍抵达洛阳郊外。远远望去,那座“正音书院”雕梁画栋,门前石狮威严,匾额乃当朝太傅亲题。阿禾下令驻扎十里外村落,每日派三人轮流潜入听课,记录讲义内容。不出所料,课程表面讲诗书礼仪,实则灌输“等级天然”“贵贱有序”“变革即祸乱”等论调,更将阿禾描绘为“妖女惑众,煽动妇孺,坏我华夏根基”。
第五日,晓禾带回惊人消息:书院地下设有密室,夜间聚集骨干弟子,宣誓效忠“复兴宗统”,并秘密编纂《新礼制草案》,主张恢复“士庶不通婚”“寒门不得任实职”“女子禁习律法”等古制。
阿禾当夜召集众人,沉声道:“他们已在织网,欲以文代武,以教代政。若放任不管,十年之后,我们将面对一群读过书、识过字,却坚信自己卑贱、理应沉默的‘顺民’。”她取出郑太和所赠竹简残片,轻轻置于案上,“这一片竹简,曾让一个家族灭门。今天我们若退让,将来会有千万孩子,永远失去知道自己是谁的机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