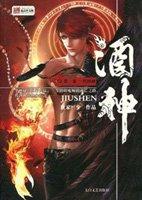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激情年代: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> 第二百四十四章 改正一些问题(第1页)
第二百四十四章 改正一些问题(第1页)
在广州的昌城汽车厂办事点工作人员都是从昌城这边调过去的,为的就是了解汽车厂内部的情况,懂得办理业务。
所以江成的出现,并没有出现办事员不认识他,然后骂他算是什么鸟东西的狗血剧情出现。
当办。。。
风在楼群间穿行,像一只无形的手抚过城市脊背。谭明远捏着那封信,指节微微发白,纸页边缘已被晨露浸出淡淡的晕痕。他没有再读第二遍,只是把它轻轻折好,放进胸前口袋??紧贴心跳的位置。
北京的秋天向来干燥,可这几日却总有些异样湿润的气息从巷口飘来,仿佛整座城都在悄悄呼吸某种久违的情感。街角便利店的老式广播突然自动开启,播放的不是广告,也不是新闻,而是一段模糊但温柔的哼唱:《月儿高》的调子,带着河北乡音的尾音微微上扬。店主愣了半晌,随后红着眼眶蹲下身,在柜台后翻出一台尘封多年的磁带录音机。
“我妈走前录的最后一盘……”他喃喃道,“我一直不敢听。”
此刻,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,一所小学的课间铃声悄然变更。不再是机械的电子音,而是由孩子们轮流录制的家人口述问候。有维吾尔族老人用沙哑的声音讲睡前故事,有汉族父亲在工地上喘着气说“娃,爸想你了”,也有母亲轻声哼着伊犁民歌。校长站在操场中央,望着一群孩子围成圆圈,手拉着手,齐声合唱一首谁也叫不出名字的摇篮曲。她的对讲机响了三次,都是上级催问是否恢复标准铃声系统。她关掉了电源,只留下一句话:“让他们唱吧,这是最真实的教育。”
而在西南山区的一所留守儿童学校里,一台太阳能收音机每天清晨准时接收一段未知频率的音频。内容从不重复:有时是某个东北母亲炖酸菜时锅盖碰撞的声响;有时是江南水乡祖母摇扇驱蚊的节奏;还有一次,整整五分钟只有火车经过铁轨的轰隆声,背景里夹杂着一个男孩断断续续的哭腔:“妈……我数学考了第一名……你能不能回来看看?”
这所学校后来被媒体称为“声音之村”。学生们开始学会用耳朵记忆亲人,哪怕从未见过面。他们不再追问“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”,而是自发组织起“声音日记”活动,把每天的心情录下来,存进一个贴满星星贴纸的铁盒子里,等待某一天能亲手交给远方的父母。
谭明远不知道这些细节,但他能感觉到。空气变了,不是温度或湿度,而是那种潜藏于人群之间的共振频率。就像暴雨前的低气压,又像黎明破晓前大地深处那一声微不可察的舒展。
他决定去一趟天津。
火车穿过华北平原时,窗外稻田泛黄,收割机在远处缓缓移动。车厢里很安静,乘客们大多戴着耳机,但没有人听流行音乐。有人闭目聆听一段老旧评剧选段,有人反复播放一段婴儿啼哭后的咯咯笑声,还有一个年轻女孩,把手机贴在耳边,听着一段明显经过多次转录、充满杂音的对话:
“小芸啊,奶奶今天包了韭菜饺子……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……可惜你在北京,吃不着热乎的……”
女孩终于忍不住,捂住嘴低声啜泣。邻座的大叔默默递上一张纸巾,自己却掏出一支口琴,轻轻吹起了《茉莉花》。音不准,节奏也不稳,但他吹得很慢,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
谭明远看着这一幕,忽然想起林婉秋说过的话:“当足够多的人愿意聆听,静默协议就会自我瓦解。”
如今,它正在崩塌。
抵达天津时已是傍晚。他按地址找到了那位老兵居住的旧式筒子楼。门没锁,虚掩着。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台灯,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:一名女兵站在边疆哨所前,怀里抱着个襁褓中的婴儿。照片下方摆着一台老式开盘录音机,磁带正在缓缓转动。
老兵坐在藤椅上,双眼失焦地望向天花板。他已经八十六岁,中风后说话困难,右手几乎不能动。但当他听见脚步声,竟猛地转过头,喉咙里发出含糊却急切的声音。
谭明远走近,在他面前蹲下。
“您还记得我吗?三个月前,我在广播里听过您唱的那首歌。”
老兵嘴唇颤抖,努力想要组织语言。最终,他抬起左手,颤巍巍地指向录音机。
谭明远按下停止键。
房间里陷入短暂寂静。
然后,老人用尽力气,哼出了第一句:
“睡吧,睡吧,我亲爱的宝贝……”
声音干涩、走调,甚至有些破音。可每一个字都像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,沉重得压人心肺。
谭明远的眼泪无声滑落。
他知道这首歌??这不是普通的摇篮曲,而是1952年抗美援朝战地医院里,护士们为孤儿集体创作的安抚调。歌词根据不同母亲的方言不断演变,旋律也没有固定版本。但它有一个共同特征:每一段结尾都会加上一句轻语:“妈妈在这儿呢。”
老人唱完,喘息良久,忽然抓住谭明远的手腕,力道大得惊人。
他张了张嘴,终于拼出几个字:
“我想……听见她叫我一声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