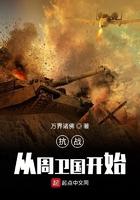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当过明星吗,你就写文娱? > 第二百二十章 把我杀了给大家助助兴(第3页)
第二百二十章 把我杀了给大家助助兴(第3页)
世界各地,无数人同时停下动作。
北京胡同里,一位老人忽然流泪:“这声音……像我妈。”
东京地铁站,一名上班族怔住:“这是我奶奶老家的调子。”
巴黎街头,留学生猛然回头:“这不是中文,可我怎么听得懂?”
而在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,那口青铜井边,沙粒开始逆流上升,聚集成人形轮廓;凉山祠堂的老鼓再度自鸣;武威荒原上,一阵清风卷起黄沙,拼出“谢谢”二字;敦煌莫高窟某间封闭多年的洞窟内,壁画上的飞天齐齐转头,面向东方。
门缓缓闭合。
余惟的身影彻底消散,唯有一根斑头雁羽毛飘落湖面,轻轻旋转,最终沉入深渊。
三天后,中科院地下实验室。
一份匿名数据包自动上传,附言仅一行字:
>“声网稳定运行中。
>守护者已就位。
>请继续记录每一个平凡的声音??它们,都是未来的种子。”
与此同时,全国多家电台陆续收到一段神秘信号,未经审批却强行插入频道。主持人声音温和依旧:
>“各位听众,这里是‘回声频率’临时广播。
>刚才播放的,是2024年冬,一位旅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首歌。
>感谢您收听。
>下一曲,来自1962年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,一位母亲与即将奔赴边疆的儿子告别对话。
>愿爱,永不静音。”
电波穿越城市、乡村、高山、海洋。
在一个小学音乐课上,孩子们跟着广播学唱这首陌生的《摇篮曲》。老师惊讶地发现,班上最内向的女孩竟然主动举手领唱,嗓音清澈如泉。
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唱,只觉得这首歌,好像从小就听过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精神病院隔离病房里,林晚忽然睁开双眼。
她嘴唇微动,无声地说了一句谁也听不见的话。
监控录像回放时,技术人员在背景噪音中提取出一段微弱音频??是余惟的声音,温柔而坚定:
>“我回来了。”
窗外,初雪静静落下。
一座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,像星辰坠地。
没有人知道,在这片土地的深处,有一条由声音编织的河,正悄然流淌,贯穿古今,连接生死,承载着所有被遗忘的言语与未说完的故事。
它不再需要名字。
因为它,就是我们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