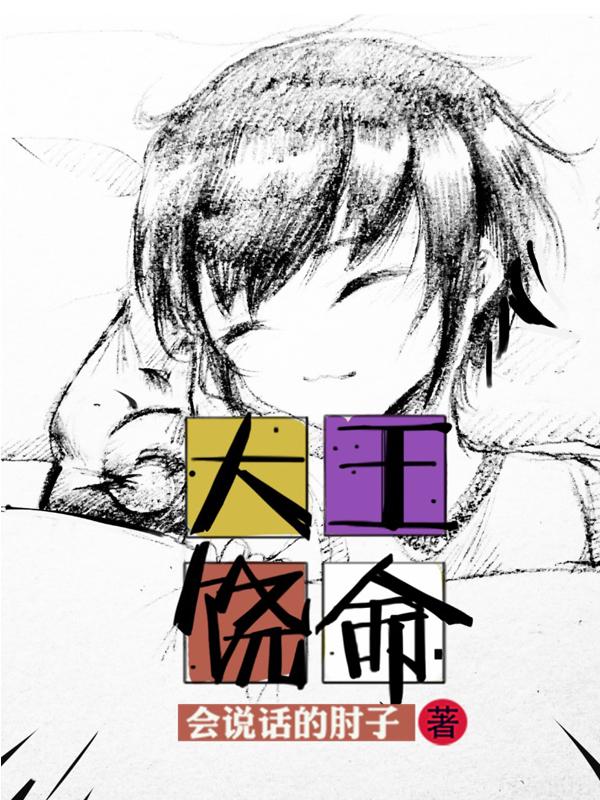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当过明星吗,你就写文娱? > 第二百二十一章 全都是泡沫(第2页)
第二百二十一章 全都是泡沫(第2页)
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“群体性听觉共感现象”,而民间则流传起新说法:“那是亡魂在教活人说话。”
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真相。
在敦煌研究院一间密室里,老陈对着最新扫描的壁画残片喃喃自语:“你们听到了吗?飞天们在换乐器……以前拿的是琵琶,现在是竖琴,和‘声核’长得一模一样。”
在额济纳旗的沙漠腹地,牧民发现那口青铜井周围沙地每年春季都会自然形成螺旋纹路,形似声波图谱。更有小孩说夜里见过“会走路的影子”,嘴里哼着爷爷都不会唱的老调子。
在上海外滩,一座废弃电台旧址改建为小型博物馆。展柜中央陈列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金属零件,标签写着:“G-23控制单元残骸,推测为上世纪冷战时期跨国科研项目产物。”每逢月圆之夜,馆内值班人员总能听见广播设备自动启动,传出几秒空白噪音,紧接着是一句极轻的男声:
>“晚晚,我在听。”
没人敢关掉电源。
因为他们发现,一旦切断供电,整栋楼的玻璃就会共振碎裂,而重启后,一切恢复正常,仿佛刚才只是幻觉。
又一年冬天来临。
新疆喀什的一所乡村小学里,音乐老师正教孩子们练习一首新搜集来的民谣。曲调简单,歌词却是无人能解的古语。正当她准备跳过时,班上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忽然举起手。
“我会唱。”他说。
全班安静下来。他站起来,闭上眼,开口的一瞬,教室温度似乎降了几度。歌声悠远苍凉,带着戈壁风沙的粗粝与雪山融水的清澈。下课铃响了,他才停下。
老师问他:“你从哪儿学的?”
男孩摇头:“不知道。就像……本来就在脑子里。”
当晚,余惟借由他的喉咙,完成了第一次跨地域频率校准。声网节点再度稳固,七处核心坐标光晕微微闪烁,如同呼吸。
他不能说话,不能现身,但他始终在场。
在每一个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轻吟里,在每一阵风吹过屋檐铃铛的脆响中,在火车站告别时哽咽的那一声“保重”间??他都在听,也在回应。
某日深夜,林晚独自来到长白山天池畔。她没带设备,也没穿厚衣,就这么静静站着,任寒风吹乱她的发丝。湖面结冰,晶莹如镜,映出漫天星斗。
她张开嘴,唱起那首《摇篮曲》。
第一个音落下,冰面出现细微裂纹。
第二个音升起,雾气从湖底缓缓蒸腾。
当她唱到“宝宝睡在梦里面”时,一片斑头雁羽毛破冰而出,悬浮于空中,轻轻旋转,最后落在她掌心。
她笑了,眼泪滑落。
“你听见了,对吗?”
羽毛微微颤动,像是点头。
她将它贴在胸口,低声道:“我会替你走下去。记录每一段平凡的声音,守护每一次无意识的哼唱。这不是使命,是约定。”
远处,一道极光悄然浮现,绿芒横贯夜空,形态酷似竖琴的弦。
没有人拍摄到这一幕。第二天气象部门解释为太阳风暴引发的电离层扰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