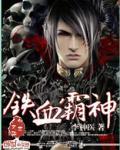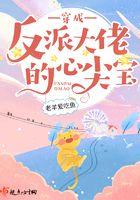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汴京食滋味 > 4550(第6页)
4550(第6页)
“我平日里偏好清静,留在身边侍候的人本就不多。那日你在祖母寿宴上见到的,大多是从沈宅喊来帮忙的。祖母走了,人也就跟着回去了。”
在江知味的搀扶下,沈寻晃晃悠悠走着,一边解释她眼中的疑虑。
听到此处,江知味却扑哧笑出声来:“觅之郎君何故隐瞒,那日并非令祖母的寿宴,这事儿,我已经从郑掌柜那儿听说了。”
她明显察觉到,搀扶着的臂膀微一发僵,旋即见他正色道:“都是祖母的一番心意,觅之为哄她老人家高兴,实在不好拆穿。”
江知味狡黠地眯了下眼:“是么,那我做的那些肠粉,可不是谢错人了?”
又凑近些,轻声道:“如此,觅之郎君可得替我好好谢谢沈老夫人。要不是她老人家,我这桩生意,还做不成哩。”
沈寻没同她对视,轻咳一声,避左右而言其他:“江娘子,咱们晡食,吃什么?”
“你想吃什么?这事儿总得由病号来决定,不过可说好,辛辣发物不许,其他随你挑拣,我都能做。”
随着慢悠悠地思索,沈寻的脚步愈见缓慢,当真一副伤了脑袋瓜以后,动脑就动不了手脚的模样:“那我想想啊……”
江知味陪他在桂花树旁想啊想。足足过了大半晌,还没见他想出分毫来。
“算了,别想了。我来吧。”
沈寻的脚步这才复又移动起来。到老槐树下,八哥鸟翠嘴的身旁,他坐下,缓缓靠在藤椅上,避开了脑袋后头受伤的地方。
红木鸟笼中的翠嘴今日很是欢脱。见人来,一个劲地“吉祥”个不停。
江知味回了句“你也吉祥”,拿起放在一旁的芦苇杆戳进笼子里逗了逗,逗得黑黢黢的小小一只踮着脚直蹦跶:“莫戳,莫戳,痒痒。”
“这鸟还真有灵性,真可爱。”她把芦苇杆放下,“我想好吃什么了,郎君且在此处等等,我去给你做晡食。”
沈
寻斜靠着,双眼静静阖上:“多谢,那就劳烦江娘子了。”
灶房里现有的食材不多,不过做个病号餐也足够了。沈寻脑袋上有外伤,要按以往那种重口刺激的口味来肯定不行。
江知味边琢磨,一边把面团子揉好。
吃面是肯定的,作为土生土长的汴京人,也就是后世的河南人,面食肯定合他的胃口。但今日这口干舌燥的,做馒头、饼子显然都不合适。
还是煮个清淡的汤饼吧。
碗里佐料配好,冲入沸水。一把葱花、半勺酱油、一勺香油、盐、糖、猪油,还有少量胡椒粉。
江知味翻箱倒柜没找到现成的胡椒,好在她随身带着那个胡椒荷包,取出来,先磨了一些,闻着喷香。
拉好煮好的面条,平平整整地铺在调好的酱油汤底中。卧上对半切开的溏心蛋,再撒上几颗点缀用的小芝麻,一碗阳春面,便大功告成了。
端到院子中时,沈寻似乎睡着了。
他的眼皮没有分毫的扇动,睫毛平稳地在面颊上匍匐,睡得很是安静。身上脏污的衣裳也已经换掉,如今又变回了先前那般衣不染尘的觅之郎君。
江知味蹑手蹑脚,不欲将他吵醒。可甫一走近,沈寻的双眼便睁开来。
与此同时,头顶挂着的八哥鸟叭叭个没完:“醒了,醒了。饿了,饿了。”
江知味仰头一看,食槽里的鸟食都空了。她把两碗阳春面放下,问沈寻:“鸟食在哪儿呢,我去找找。”
沈寻刚睡醒,人还有些懵,这会子是真的头脑发昏,手臂轻颤,往石桌下一指:“就在这儿,一次喂一杯粟米就成,吃完了再添。那水,翠嘴它不喝溪里井里的生水,只喝半温热的,每日得添个两回。”
“这鸟还有名字,翠嘴,可它的嘴也不是绿的啊。”江知味嘟囔着,都依言照做,等回来时,沈寻面前的阳春面还是没动。
“怎的,这汤饼太清淡了不合胃口?再不吃就放坨了,可不好吃了。”
“总得等江娘子来,一起吃才好。”
江知味赶紧落座:“我都忘了,你们富贵人家规矩多。要早点说,我就先陪你把汤饼吃了,再去捣鼓鸟食了。”
沈寻施施然握住筷子:“这会子刚好。江娘子,不知这道汤饼,可有名字?”
说起名字,江知味猛然想起家里的那只“刘海”,想来这鸟名也是觅之郎君取的,这会子问起汤饼的名字,不会是打算给汤饼也取个名吧。
赶紧解释了:“有的有的,阳春汤饼。”
沈寻微微一笑:“好听,是江娘子自己取的?我在汴京,可没见过阳春汤饼这道吃食。”
“倒不是。”江知味吸溜了一大口阳春面,在嘴里嚼了咽下,“这是南方两浙路的吃食。南方嘛,孟冬时节,天气转冷之前,会有一段时间如春日一般温暖,当地人称之为‘小阳春’,这汤饼就是在那个时节吃的,故而得名。”
沈寻轻点两下头:“原是如此。那而今,在汴京的十月,吃这阳春汤饼也是刚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