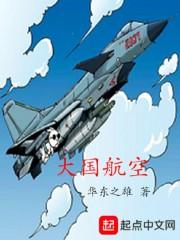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汴京食滋味 > 5055(第10页)
5055(第10页)
王婶一口应下,顺道也帮吴用应下了。
毕竟江知味这人不白叫,都是给工钱的,一天一百文,能抵整天的营收,还不费力,多美的事,去,指定去。
江知味叫的这几个,都是在汴京城里没甚亲戚走的。
到初三那天,租了辆三头驴拉的大车,把一行人都载到了食肆,顺带扛过去的,还有今日午后要做的吃食。都是第一回到食肆参观,正好开个锅,叫大家伙儿在店里先坐坐。
来应聘的几个小伙子小娘子都到了。一共八人,在店门前歪歪斜斜站着坐着。
江知味在车里吩咐了,今日是八进三,挑的是店里的账房和杂工。
论算账这事儿,周婶有经验。问没几句,就给江知味选出了一位名唤薛莹的年轻娘子。此人口齿伶俐,脑瓜子也活。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,百贯千贯的账面,两下就算齐活了。
关键性子不赖,早前也有在脚店里头当账房的经验。可惜那前掌柜是个酷爱欺负小娘子的老头,没干多久,就总想对她上下其手。
薛莹不堪受扰,工钱都没要就着急忙慌地跑掉,正担心没地儿落脚,就看到了知味食肆招人的告示。
至于跑堂,宋时的端菜跑堂就跟耍杂技似的,江知味这食肆规模不小,客人多,跑堂记菜得记性好、识字、嘴甜,臂力脚力俱佳,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就能跑的。
一来二去的,定下来两个。
一个叫薛虎,这名字巧了,跟薛莹兄妹似的,不过并没有血缘关系。长得虎背熊腰、膀大腰圆,看起来还挺唬人。
但性子却跟老龟似的温和,长了一双无比宽厚的大手,只一边胳膊,就能托起二三十个盛满了汤水的陶碗。当场试过,走得稳稳当当。
另一位是上了年纪的妇人,陈虞婶。说是年轻时候干多了针线活,眼睛花了没钱治,成了个半瞎。但看些大的东西没甚问题,手指头也灵活,想来谋个专门负责洒扫的活计。
江知味原本犹豫,怕她佝偻着身子、眼睛还雾蒙蒙的干活不利索。
没想到陈虞婶的力气奇大,走起路来虎虎生风,一点儿不像眼睛看不见的样子。洗碗也是,比那几位眼睛好的更麻利,嗖嗖几下,洗得干净又锃亮。
讨论之下,最终还是留下了。
这三位,只有薛莹一人无处可去,需要在食肆里头住宿。
江知味本就预留了供员工居住的屋子。偌大的食肆,夜里总是有人需要看着的。有薛莹在,正好可以防着食肆里的一些突发情况。
其他人,就陈虞婶住得远些。不过陈虞婶表示可以早起,跟他的儿子,一位在木匠家里做工的学徒一并进到内城,不会耽搁食肆的生意。
签完工契,该回去的就先回去了。薛莹的铺盖都在边上放着,江知味领她去了后堂安顿。
正好要给食肆开锅,薛莹便一块儿,尝尝他们家掌柜兼主厨的手艺。
这时候,江知味特意找许木匠定做的桌子就派上了用场。
桌子中间,挖了两个大洞,可供放置炭盆。一边架上铁篦子,把桌子里头直通地下的烟道一开,可以烤肉。另一边,放定制的大砂锅,能煮拨霞供、砂锅粥、砂锅面。
要不想开火,只想吃点儿爊肉、炒菜,就用一块平坦的草编盖板,把那两个窟窿盖上。能把上面的碗盘托得稳稳的,里头的炭盆,也不至于溅汤、落灰。
来时,周婶他们就被食肆里新奇的装潢震惊到了。不仅这些摆在大堂里的桌子,整个食肆,都和他们想象的不大一样。
进门是一大片的快食区,占了半间屋子。用木头做了个对外开敞的餐食架子,看起来像是在食肆这间大的铺子里安上了一座小房子。
小房子的顶上,挂了大张大张的字画,江知味介绍,这是店里的招牌菜展示。字画都用木框裱起,开业以后,就把框裱后头藏着的烛火点上。
借着烛火的暖光,这些字画上的吃食无论在食肆的哪个角落,看着都格外明亮。
比如那酸萝卜老鸭汤,上面的萝卜、鸭肉都带着一股子新鲜劲儿。还有那酱大骨,也都是画得根根分明,连骨头里的骨髓,都特意画出了。
江知味自个儿不会画画,这些,都是连池来讨要吃食时,她请沈寻留的墨宝。没想到二人虽未碰面,仅凭她的口述,沈寻也能把这些吃食画出她心目中的那个样。
不像国画的画风,倒更像西洋画了。
快食区主要上一些提前炒制的菜品,有些客人,尤其是赶着吃完了去做工的客人,等不及现炒现吃,那就到快食区挑拣吃食。
快食区的桌板上都有凹槽,这些凹槽里到时会灌上滚水,给上面的菜品保温。这样就算菜是提前做出来的,客人们也都能吃上一口热乎的。
再往里就是餐桌、餐椅了。
都是烤肉、拨霞供一体的。考虑到吃烤肉时的排烟,烟道都做在了靠墙初,也不知胡六和许木匠琢磨出了一个什么机关,竟能不借助风扇,把原本上旋的烟气往地下导。
食肆深处,用屏风做了两个隔断,当包厢使用,用的也是一体化桌子,只不过外头用的是方桌,里面是圆桌。桌腿上都雕了花脚,看着更比外头更气派,符合这时候达官贵人的审美。
在街邻们的“哇”声一片中,江知味把准备好的糟粕醋锅底端出来。
薛莹当下便已经进入了状态,也不管自
己是食肆的账房还是跑堂了,收拾完细软、铺盖,便帮着江知味忙前忙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