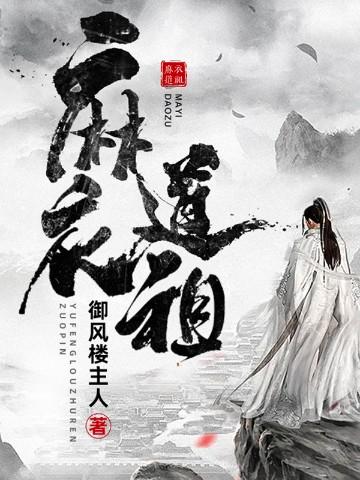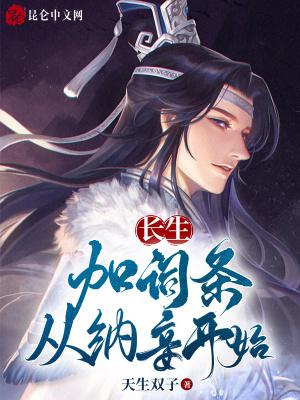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相国在上 > 244不负(第1页)
244不负(第1页)
听雨轩外,芸儿两只手绞在一起,在廊下来回踱步,小脸上满是纠结之色。
方才杜氏叮嘱她好生侍候小姐,芸儿自然明白这是何意。
虽说薛沈两家已经定亲,但才到第二步问名,后面还有一堆仪程,两个年轻人。。。
夜色如墨,深沉得仿佛能吞噬一切。相国府内,烛火摇曳,映照出一道瘦削却挺拔的身影。沈砚站在书房窗前,手中握着一封密信,指节微微发白。窗外风声簌簌,吹动檐角铜铃轻响,如同命运的低语,在耳畔萦绕不去。
这封信来自北境边关,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??“敌军压境,粮道断绝,守将请命回援”。短短十二字,背后却是十万将士的性命与大胤江山的安危。沈砚闭了闭眼,眉心紧锁。他知道,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边境冲突,而是蛰伏多年的北狄终于撕下伪装,举兵南下。
而朝中……朝中却还在为立储之事争执不休。
三日前,圣上突发风疾,昏迷两日方醒,醒来后神志不清,连太子之名都唤不出。于是朝堂之上,皇子们各怀心思,党羽林立,明争暗斗愈演愈烈。二皇子萧景珩打着“清君侧”旗号,暗中联络禁军将领;四皇子萧景昀则以孝治天下自居,日日侍奉汤药,博取清名;唯有太子萧景渊,自事发以来闭门不出,仅遣心腹探望父皇,言行谨慎至极。
沈砚是先帝托孤之臣,官居相国,执掌中枢,本应主持大局。可如今他却如履薄冰。一则因他权势太重,早已惹人忌惮;二则因他与太子私交甚笃,外人皆道他是太子党羽,哪怕他屡次上疏请求避嫌,也无人相信。
“大人。”门外传来低沉的声音,是他的贴身幕僚陈砚舟。
“进来。”
门开一线,陈砚舟快步而入,衣袍带进一阵寒气。“北境八百里加急,又来了一封。”他递上另一封火漆封印的军报,“这一次,雁门关失守了。”
沈砚猛地转身,目光如刀。他接过军报,拆开一看,心头骤然一沉。雁门关乃咽喉要地,一旦失守,敌军便可长驱直入中原腹地。更糟的是,守将周崇武战死,首级被悬于城楼,士气尽丧。
“传令下去,明日早朝,我将奏请亲征。”
陈砚舟一惊:“大人!您乃国之柱石,岂可轻涉险地?再者……陛下未醒,朝局未定,此时出京,恐有变数。”
沈砚冷笑一声:“若等朝局定了,北境怕已沦陷千里。国难当前,哪还有工夫计较个人安危?”
他说完,踱步至案前,提笔疾书,拟写奏章。笔锋凌厉,字字如剑。写罢,吹干墨迹,放入紫檀木匣中锁好。
“另外,派人去太子府,约他今夜子时相见,地点……就定在城西破庙。”
陈砚舟迟疑:“那地方荒废多年,阴森得很,是否换个……”
“正因荒凉,才无人耳目。”沈砚打断他,“此事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记住,只许你亲自去,回来后立刻烧掉联络的暗记。”
陈砚舟点头退下。
沈砚独自伫立良久,望着窗外一轮残月,忽觉疲惫如潮水般涌来。他不是不怕死,而是怕死得毫无意义。当年先帝临终握着他的手说:“沈卿,朕把江山和儿子都交给你了。”那一瞬,他跪在地上,泪流满面,发誓不负所托。
可如今,山河动荡,储位未定,奸佞环伺,他该如何护住那个温润如玉、心怀苍生的太子?
子时将至。
城西废弃的土地庙早已倾颓不堪,杂草丛生,蛛网密布。沈砚披着黑袍,悄然踏入庙中。香炉倒伏,神像蒙尘,唯有月光透过破瓦洒下斑驳光影。
不多时,脚步声由远及近。
一人缓步而来,玄色长衫,腰佩青玉,面容清俊,眉宇间自带一股沉静之气。正是太子萧景渊。
“老师。”他低声唤道,声音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。
沈砚上前一步,深深一揖:“殿下。”
两人对视片刻,无需多言,彼此心中已有千言万语。
“北境战况,我已知晓。”萧景渊率先开口,“老师欲亲征,可是为了逼宫?”
沈砚一怔,随即苦笑:“殿下聪慧过人。不错,若我不走这一遭,只怕有人要在京中动手了。”
“二哥已经联络了左骁卫将军李承?,昨夜密会于醉仙楼。”萧景渊缓缓道,“四弟也不安分,今日向礼部尚书提议提前举行祭天大典,名为祈福,实则想借机掌控太庙兵符。”
沈砚冷哼:“好一个兄弟情深。”
“老师打算如何应对?”萧景渊问。
“我明日上奏,请旨出征,率三万禁军北上抗敌。”沈砚目光坚定,“只要我离开京城,他们便会放松警惕。届时,殿下只需按兵不动,静观其变。待我在外站稳脚跟,便可调兵回援,一举平定内乱。”
萧景渊沉默片刻,忽然道:“可若父皇在此期间驾崩呢?”
空气瞬间凝固。
沈砚缓缓抬头,看着眼前这个曾被他一手教导的年轻人。他记得十年前,那孩子捧着《春秋》问他:“先生,何为忠?”
他答:“尽己之心,谓之忠。”